以真理为导向的能力
历史学家一致认为,林肯做决策非常审慎,注重分析和考量各种不同的意见和证据。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到1854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制定时,林肯已经在考虑和奴隶制有关的道德问题,他试图先在自己头脑中找到某种解决方案。林肯写下了两份笔记,其中他反复斟酌支持奴隶制的各种不同论据,测试其中是否蕴含正确和合理之处。在其中一份笔记中,他评论道:“尽管证明奴隶制是一件好事情的作品已经汗牛充栋了,但是我们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个希望受益于奴隶制的人甘愿把自己变成一个奴隶。”
随着林肯逐渐地确立在废奴问题上的立场,他试图将自己与耳闻目睹的正确的道德准则关联起来,特别是与《独立宣言》作为一种理想提出的平等原则关联起来。林肯反复衡量各种不同的选择,全面考虑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深入思考内战背后更大的道德问题,这一切都说明他希望做出正确的决策,而不只是权宜之计。
行必果、果必正的能力
林肯最终完成了保卫联邦的首要使命,也通过战争的方法解决了奴隶制问题。正如我们在这一部分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林肯的领导力那样,他在整个总统任期一直努力实现其最初设定并不断修正的目标。不论是挑选内阁成员还是权衡《废奴宣言》的发布时机,林肯都展示出了高度的政治敏锐性,这种天赋使得他在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获得了相对广泛的支持。通过吸取自己在任命军队将领时所犯错误的教训,林肯最终找到了最合适的人选,可以根据原先设定的目标和策略来作战。他在军事领导力方面的变化,以及他在军事战略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的增长,都使得整个战争朝着有利于联邦的方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林肯只聚焦于几个少而精的目标,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然这种成功也包含了一定的变通性和灵活性,更包含了对权力的局限性的认识。正如詹姆斯·麦克皮尔森所评论的那样,“他清楚地阐述了一个毫不含糊的国家政策,而且通过试错的方式不断地优化国家战略和军事策略,从而实现政策目标。我们的国家并没有因此从地球上消失,反而经历了一场自由的重生。”
应对逆境的能力
有些学者推断说,林肯早年的生活经历为他后来经受国家分裂和战争的考验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亚伯拉罕·林肯早年生活坎坷。9岁时他就经历了身边很多亲人先后亡故。他的母亲去世了。在这之前,他还在襁褓中的弟弟就早夭了。当他19岁时,他的姐姐又死于难产。雪上加霜的是,1835年,就在他准备结婚时,其未婚妻安妮·拉特利奇却撒手人寰。
这一系列的人生惨痛对林肯造成了深重的影响。桃乐斯·科恩斯·戈德温认为,“林肯早期经历的人生悲剧加重了他固有的忧郁气质。但是,他对痛苦和失望的了然也赋予了他超人的勇气,使他对人的脆弱有了更深的体悟……而且,林肯天生就有源于生活的幽默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这使得他能够坚定意志,走出绝望。”戈德温用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在《童年·少年·青年》一书中,托尔斯泰探讨了一个人潜在的爱的能力和对深重的个人悲剧带来的创痛的修复能力之间的关系:
只有那些能够强烈地爱的人才能经受得住撕心裂肺的悲痛。但是,他们施爱的强烈愿望有时候可以让他们摆脱悲痛,获得自我拯救。在人类的生命中,道德机能比生理机能更坚韧、更顽强,要知道,悲痛从来无法将人葬送。
托尔斯泰的这一说法为林肯之所以有能力克服无数悲剧提供了有力的解释。林肯应对逆境的能力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他坚信的宿命论,这一点林肯自己是承认的,其同时代人也证实了。他认为,人在很多事情上的主观能动性是非常有限的,所有事件都是由“神圣的天命”或者上帝的旨意来掌控的。这一独特的神学理念使得他能够将各种悲剧事件视为不可避免的,而不是人类的行为可以影响的。这样一种信仰体系大大地增强林肯面对不断加剧的伤亡状况的能力,因为这场战争比预想的时间要长得多。在其第二任总统就职典礼的致辞中,林肯认为冲突的根源是人为的问题(奴隶制),但是惩罚(战争带来的伤亡和战争的旷日持久)则是上帝所为:“全能的上帝自有其目的。”正如唐纳德所总结的那样,“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样一个理念:在战争所有的挣扎和损伤的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是神圣的旨意。”林肯的神学理念使他得以将对战争和其他事件所引发的惨剧的谴责从人的行为转向了干预尘世的上帝及其神秘莫测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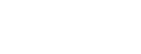
 问答
问答 创业社区
创业社区 创业学堂
创业学堂 讲师团
讲师团 我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