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将谈一谈德鲁克自己在一系列职业中——包括作为通用管理领域的教育家和顾问——对学习观的实践。简单来说,德鲁克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学习习惯,这种习惯不仅涉及管理学的方方面面,还包括如何整合包括艺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类的子领域中的知识。德鲁克的方法简单而直接。他给自己的计划,是每三年掌握一个新领域和新学科的基础知识。他的目的并非成为该领域的大师,而只是学到一定程度,从而使他能够思考该领域的关键问题,能够探索如何将该领域的知识移植到通用管理领域的程度,并且反过来思考如何将通用管理领域的知识运用到这一领域。[12]这就是为什么把德鲁克的作品当成管理学或领导学的方法手册来读是没办法理解他的观点的。德鲁克对管理学的洞见,总是根植于对宽广格局的分析,这种分析涉及的是某一时间点社会的整体需求,而不仅仅是经济。换句话说,德鲁克总是乐于通过背景来思考问题,他希望自己的读者能够努力地将管理学方法看作社会问题的需求与回应而加以理解。将经济和组织问题置于社会现实的背景之下理解,是德鲁克为自己设立的挑战之一。[13]
学会修通
德鲁克就是通过这样的智识交换开始自学的。由这一过程,我们得以管窥他的学习观。但这种在不同学科间知识的互通不等于产生知识,而是与研究各种不同领域知识相适应的一种方法。这种对不同领域知识内容的研究和学习远不仅仅是简单地容忍歧义、模棱两可、变化与不确定等,而是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必要的注意力,能够将各类知识融会贯通,实现“知识的广泛性”,同时还不会遭受认知失调。换句话说,德鲁克身上具备组织和管理变化领域文献中所谓的“消极能力”。[14]尽管这个词并非德鲁克本人的发明,但考虑到他后来支持的学习模式,这种能力显然是他希望自己的读者能够培养的。
拥有消极能力的人能够“保持和保有”,其对象不光是知识,还有跟知识或与其相关的背景的影响。换句话说,这种保持和保有的能力也就是弗洛伊德修通概念中涉及的心理机制。[15]然而,修通这一概念并非只是一种安全机制,是某一结构中的安全网; 更重要的是,修通还是一种精神分析法,前提是它不仅能够对人过往的经历产生影响,还代表了主体愿意通过对记忆的重塑来为自己的身份认同负责,以防止堕入原始创伤之中。换句话说,弗洛伊德所说的主体,必须要有所“记忆”,必须要说出自己的心理创伤,以避免反复受伤的危险。对创伤情形的描述本身并不具有治疗作用;心理创伤情形需要得到修通,促使病人灵魂深处与“文字”相关的影响能够得以清理,甚至重塑,这样能够使病人能够更好的处理这些影响。[16]
学习与创伤
基于德鲁克在著作中谈到的学习观,我想要论述的点在于,学习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可以导致心灵影响的,因为学习不仅对头脑提出了要求,还对心灵有所要求。知识工作者或知识学者必须保留和保有在一定学习背景下所学到的知识,而这并非易事,除非他们学习的时候采用的是主题索引这样简单的方式。任何在复杂程度上超越主题索引的学习方法,都是可以导致创伤,可以影响内心情感的;因此,人们必须学会保留和保有,同时不诉诸自我防御机制。在德鲁克的理论模型下,学习导向可以通过不断让管理者接触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来约束这种自我中心的心态。
这也意味着,学者更愿意以时间维度思考问题,而不是天马行空地在空间和脑海中竭尽想象,即使后者更有诱惑力。学习过程中产生的情感方面的挑战,是以时间性的方式向学习者提出要求的,而并非通过常规的分类法,后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一直是整理知识的常用结构。德鲁克在这一点上并没有非常直接地点明,因为就这一问题来看,他比较希望知识工作者即便在对学习不感兴趣的时候,也能表现出兴趣。这部分是因为德鲁克作为知识工作者,需要对知识工作者这一群体形成“投射性的身份认同”。此外,德鲁克主要感兴趣的是学习过程,而不是从学习模式中可以展现的主体性内容的预设。
德鲁克与弗洛伊德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之所以对主体性感兴趣,仅仅是因为他认为知识工作者可以将自己作为学习知识的对象。换言之,主体性之于德鲁克,只是获取知识的手段,是领略学习过程所带来的快乐的方法。而弗洛伊德之所以对学习理论感兴趣,仅仅是想知道学习理论能为超心理学带来什么,而这对于主体性理论又有何影响。换言之,在精神分析领域看来,对自我的认识是主体同时表现出渴望和抗拒的对象。正是自我认知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与无意识之间的联系,使得主体激烈地对这种认识提出表达出抗拒。不是说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个人不会或不愿学习知识;而是说弗洛伊德理论下的主体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无意识只有在自己愿意的时候才会提供知识。[17]换句话说,无意识的袒露并不受认识主体有意识的控制;有意识主体应该就无意识的这种袒露反向地构建自我认识。而这一过程就是学习带来的创伤。
[12]见德鲁克, 彼得 F (1997). “重新发现个体,” 《德鲁克论亚洲: 彼得·德鲁克对话中内功》,牛津: 巴特沃斯-海尼曼出版社, 105.
[13].德鲁克认为,在日本这样的国家,将社会优先于经济考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美国当然也完全可以这样。当然,德鲁克这么想有些异端,因为他正是凭着自己的不顺从,凭着自己对当下正统观点的反对,才得以采取社会经济的角度对自己的领域进行观察。而且,即便在“咆哮的九十年代”之后,连当代的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都开始宣扬经济优先于社会了,我们仍然应该记住,“在美国,认为经济优先于公共生活和公共政策这样的观点仍是比较新的,最多不过追溯到二战。在那之前,就连美国也是优先考虑社会的。即便是遇上了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也是将社会改革放在经济复苏之前的。而且当时美国的选民们非常认同这一做法。”见德鲁克, 彼得·F (2002). “社会优先” 载于《下一个社会的管理》, 222.
[14]这一概念最开始是由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提出的,之后被罗伯特·弗兰奇引入组织学理论中。见弗兰奇, 罗伯特 (2001). “‘消极能力:’管理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组织变化管理学期刊, 14 (5), 480-492.
[15]关于“修通”,见拉普兰琪, J与庞塔利斯, J-B (1988). 精神分析学的话语, 由史密斯, 唐纳德·尼克尔森译, 伦敦: 卡纳克图书及精神分析学院, 488-489.
[16]我所说的letter一词,并不是指在邮政系统中传递的那种文件,而是指字面上的意思,也就是字母表里的字母。这些字母能够深入主体的内心深处,通过某种形式的功能紊乱,形成生理或心理上的某种症状。以雅克·拉康的理论为基础,拉康最早的学生之一赛尔吉·勒克莱为了发展出非阐释性的精神分析理论,对内心深处这种“不合常理的”的事情所扮演的角色做了精确的研究。有关这种文字的医学案例以及文字在症状理论中的地位,见勒克莱, 赛尔吉 (1998). 精神分析: 论无意识的顺序及文字的方法,由卡姆福, 佩吉译. 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多处涉及.
[17]见费尔曼, 肖莎娜 (1987). 雅克·拉康与洞见带来的冒险. 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多出涉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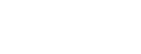
 问答
问答 创业社区
创业社区 创业学堂
创业学堂 讲师团
讲师团 我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