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学习
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德鲁克作品中体现的预设,都是主体究其定义而言就是认同学习的可能性的。这跟弗洛伊德理论下的主体正相反,后者的标志是抑制,即对知识的拒绝而非接受。[18]当然,知识跟学习有所不同,而拒绝知识也不一定就是拒绝学习。尽管如此,只要我们能在知识与学习之间建立起连续性(了解到前者是结果,而后者是过程),就必须将认识主体放在探索与拒绝的矛盾下来讨论。认识主体并不选择探索或拒绝,其态度是模棱两可的,而这正反映了学习主体的创伤,学习主体必须解决自己对自己努力——即知识——的内在抗拒。不过,有趣的是,德鲁克与弗洛伊德似乎有一点共识:学习及分析的目的在于对认识主体进行更新。[19]换句话说,两者都认为,学习行为本身内在地具有治愈功效;当然,学习行为不能保证产生这一作用,自不必多言。
就本文关注的内容而言,上述著作对管理学的意义在于,现如今的世界强调“创造性破坏”,竞争也日益激烈,而知识工作者与组织的责任,就在于去探索学习是否真的能够成为个人和企业更新的方式,并探索能够实现这种更新所必须的方法。[20]对德鲁克而言,知识工作者寻求更新的秘诀在于“知识的广泛性”。有趣的是,德鲁克学习理论的基础是知识工作者工作寿命的增长,而弗洛伊德则认为无意识并不涉及时间。
虽然德鲁克与弗洛伊德可能对时间有不同的理解,探讨时间如何影响学习行为,还是十分有意义的,尤其是探讨精神分析学中提到的欲望的真相,因为了解这一真相能够使主体更好地理解自己行为的重要意义。毕竟,成人教育界的学生最常问老师、老师也最常解答的问题之一就是:我现在学习晚吗?学生总是能够得到宽慰之词,告诉他们学习永远不嫌晚!当然了,这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并不表示说出这句话的教师对学习的时间性问题有过什么思考。对德鲁克而言,学习是欲望的客体;而对弗洛伊德而言,欲望是学习的客体。德鲁克理论下的主体对学习产生欲望;弗洛伊德理论下的主体对欲望加以学习。认识主体的更新,也就是所谓知识工作者的命运,就依赖于何时培养学习及/或欲望。
不过,在此之前,有必要了解德鲁克对知识与欲望之间关系的理解。尽管德鲁克曾经在书中花了一章来写弗洛伊德,他更多的是将弗洛伊德作为当时维也纳的内科大夫在描写,而并不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本身的阅读心得。德鲁克感兴趣的主要是弗洛伊德有关个性的元素,(在其自我分析中不存在),而并不太关心精神分析学中的相关概念(如果有的话)对于管理学或组织学的意义。德鲁克并没有在其作品中阐述管理与精神分析之间的关系——至少没有正式讨论,尽管他祖籍维也纳,也花了时间去读弗洛伊德的作品。全文的亮点,就是德鲁克描述了自己八九岁的时候,跟弗洛伊德在维也纳贝尔加斯的家附近的一家餐厅相遇的场景。[21]
因此,如果说德鲁克建立了欲望理论的话,这一理论必须再考察他早期的七次经历之后加以重塑。他曾在一篇主张重塑自我的文章中提到了这七次经历。下面我会讲述这几次经历,并分析它们之间的共性,总结知识工作者可以从中受到的启发。换句话说,德鲁克并没有对如何运用精神分析法给予太多关注,而更在意将该方法置于弗洛伊德生活的维也纳来考虑。但德鲁克以往在文章中提到,需要对弗洛伊德加以分析,他也曾用弗洛伊德的机制来阐释过弗洛伊德的一生。他并未将精神分析法当作医学和文化学阐释的重要工具,反而认为这一方法“只能靠对较难问题的回避,来维系笛卡尔式的理性世界与灵魂深处的黑暗世界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他仍然觉得精神分析法“令人着迷,入木三分,而且也相当感人。”[22]
[18] 抑制一词在这里是指结构性的抑制。换言之,所有主体都受到这种初级抑制的影响。随后对知识的拒绝则是由于次级而非初级抑制的影响,因为抑制不仅是一种原始的反应,还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与该主体力比多经济学及心理花费的结构有关。见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 (1915). “抑制”, 载于论超心理学: 精神分析理论, 由斯特拉奇,詹姆斯译, 理查兹,安吉拉编. 伦敦: 企鹅出版社, 1991, 139-158.也可见拉康, 雅克 (1979). “从解释到移情,” 精神分析中的四个基本概念, 由谢里丹, 亚伦译, 米勒, 雅克-阿兰编.伦敦: 企鹅出版社, 251-52.
[19] 在学习组织的理论中,一个核心的假设就是个人与企业的更新与学习过程有关,或可以跟学习过程有关。如今这一话题存在大量文献。这里的核心问题则在于如何调和两种有关主体的概念之间乍一看存在的矛盾(经济主体与学习主体)。比如,有些企业领袖重新定义了自己的组织,认为自己的组织可以按照大学的模式运作,学者对此十分高兴。有关学习组织的理论(阿里•德•赫斯及彼得·圣吉的作品中有所涉及)和有关公司的管理学理论(克里斯托弗·巴雷特与苏曼特拉·格沙尔的作品中有所涉及)都极其关心学习与更新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比如,可见苏曼特拉·格沙尔论管理: 善良之力的第6章与第7章, 由布尔津肖, 朱利安与皮拉玛尔, 基塔编(2005). 伦敦: FT 普伦蒂斯·霍尔出版公司, 131-184.也可见格沙尔, 苏曼特拉与巴雷特, 克里斯托弗 A (1999). 个人化的企业, 纽约: 哈珀商业出版公司, 69-137.
[20] 福斯特, 理查德 N与卡普兰, 萨拉 (2001). 创造性破坏: 从为持久建造到为绩效建造, 伦敦: FT 普伦蒂斯·霍尔出版公司.
[21] 见德鲁克, 彼得 F (1979). “真假弗洛伊德,” 载于《旁观者》, 伦敦: 威廉·海曼出版公司, 印度重印版, 新德里, 1980, 83-99.弗洛伊德本人并未接受过精神分析,而是做过自我分析,这一点引起了其后的学者极大的理论兴趣。拉康在讨论到癔病的时候曾有如此论述,“我认为,癔病让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就带上了原罪。某种原罪必定存在。真想可能很简单,那就是,弗洛伊德本人的欲望,弗洛伊德本人心里的一些东西,是从未受到分析的。”见拉康, 雅克 (1979). 精神分析中的四个基本概念, 12.
[22] 见德鲁克, 彼得 F (1979). “真假弗洛伊德,” 载于《旁观者》, 99. 读者如果想了解德鲁克笔下弗洛伊德时期的维也纳,或者想要了解翻译弗洛伊德的译者在其理论框架上偷偷掺假的医学术语以及由此带来的混淆,可见伯德令, 布鲁诺 (1982). 弗洛伊德与人的灵魂, 伦敦: 企鹅出版社. 伯德令是弗洛伊德与德鲁克的同代人,他曾讨论过一些文化上的焦虑,即弗洛伊德究竟会作为医生还是作家而受人铭记,以及这样的认识论会对精神分析理论基础方面的讨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令人惊讶的是,德鲁克并未提到任何伯德令在上述著作中涉及的翻译问题,尤其考虑到两人都来自维也纳,都说德语,且都在美国凭其各自的专业领域而为人所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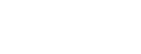
 问答
问答 创业社区
创业社区 创业学堂
创业学堂 讲师团
讲师团 我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