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的时候,蓝领工人还是无产阶级。劳工组织要么完全非法,要么不受待见。那时候没有工作保障,没有八小时工作制,谈不上健康保险(德国除外)。而五十年之后,蓝领工人几乎占据了所有的发达社会。
而现在,我们的劳工部长在《国家的工作》一书里公开宣称蓝领工人已经不重要了。劳工组织也接纳了他的话。
施:不过新政府也提到,有一些蓝领工人的工作还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薪资较高的制造行业。克林顿一直在这么说。你觉得他这么说真的是在误导大家吗?
德:不管这一届政府怎么说,我们这个十年到头的时候,在三大汽车公司工作的人数将只有现在的1/3,或者可能只有40%。而日本的汽车公司也不会再持续增长了。
我不觉得这届政府能为此做什么。如果这届政府妄图阻止这些旧产业围绕知识进行重组,那这些工作只能流向海外。道理就这么简单。我们在重组的道路上已经走了挺远了。美国钢铁公司1980年的时候有120,000名炼钢工人,如今只有20,000名,产量却能保持不变。
这场转变在我们国家尤其是个问题。因为过去四十年间,一个黑人的工资能迅速跃升至中产阶级,甚至跻身上流,靠的就是在生产线上的工作。所以这一转变可能加剧种族歧视,而种族歧视已经够严重的了。
不过我认为我们在这条路上已经远远领先了,我们的重组工作已经完成了2/3。而日本和德国的重组还没起步。日本人现在开始正视这个问题了。他们希望人口结构——由老龄化人口带来的劳动力短缺——能够对他们有所帮助。同时,日本人还有个规矩。你要是上过高中了,就别当蓝领工人了,你得去做文职工作。要是上了大学,就必须去做专业人士或管理人员。而现在日本几乎人人都上过高中了,文职人员和管理人员严重过剩。你要知道,日本公司管理层的过剩现象简直难以置信。
施:这是不是因为同样的稳定机制,在一个环境里可能是好事,而到了另一个环境就可能造成麻烦?
德:正是如此。说起来,日本的终身工作制,很大程度上还与我有关(倒不是全都该由我负责)。四十年前,我主张公司应该保证薪水、保证工作、保证收入。日本人听进去了。二战期间日本劳动力极其短缺,各个行业都不断涨薪来赢取工人,日本军队只好颁布了一条命令:有工作的人不准离职。不准。然而,二战之后,日本迫切想要摆脱这条命令。为此,尼桑的员工曾经组织了一场很大的罢工,最后工会还输了。
那时候,我和其他一些人告诉日本人,如果你们想要确保和平的劳资关系,就必须得提供工作保障;不是给每个人都提供,但要给那一小部分核心的、终身的员工。
现在回头再看,我当时也犯了些错。那时候给日本人这么讲是对的,但给美国的管理者也这么讲,这不太对。美国的工人适应性和流动性都很强。在扬斯敦、底特律这样的地方,几乎没有永久性失业的人,这简直令人惊讶。不可思议。
美国工人的流动性和适应能力非常强,这也使我们免遭很多社会问题。而日本接下来几年可能会相当困难。
生产力与知识工作者
施:你我都是知识工作者。制片厂、医院、大学、研发组织、软件开发商、政府和执法部门、报社、出版社,这些机构都是知识组织。然而,这些产业生产力低下也是有目共睹的。假设知识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要提高收入应该先提高生产力是正确的,我们如何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呢?我们如何提高研究人员、编辑部、咨询团队的生产力?重要的是,如何提高行政管理层——这些最没有生产力的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呢?
德:这个问题有两面。当初费雷德里克·泰勒研究铸铁厂里那些铲沙子的伙计的时候,泰勒本人或是其他任何人都未曾考虑过这些人在做的这件事本身。这是个铸铁厂,你需要沙子,需要把采石场里的沙子铲到别处。对此没有人有什么意见。这件事情本身是预先就确定了的。问题在于如何去做这件事。
而对于知识工作,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你应该做什么?”不是如何做。无论在天堂还是人间,要是一个富有激情、具备专业水平和勤劳精神的工程部门去为一个错误的产品画设计图,也会索然无味。要提高知识的生产力,首要问题就是该做什么。这是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但也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 1: 《理解生产率》学习计划内(一)
- 2: 德鲁克:生产率:管理能力的第一
- 3: 德鲁克:财富创造资源的创造性运
- 4: 德鲁克:“新的价值
- 5: 看懂生产率:入门读物,加拿大统
- 6: 浅谈数字生产率,”
- 7: 威廉·鲍莫尔:&
- 8: 《理解生产率》学习计划内(二)
- 9: 教务通知(1)
- 10: 《理解生产率》学习计划(三)
- 11: 德鲁克:“生产率的
- 12: 德鲁克在哈佛肯尼迪学院的讲演:
- 13: 德鲁克:《21 世纪的管理挑战
- 14: 《德鲁克经典管理案例解析》案例
- 15: 柯赫:《做大利润》第四章 摆脱
- 16: 柯赫:《做大利润》第八章 知
- 17: 威廉姆·麦克格恩
- 18: 国企改革—&mda
- 19: 彼得·施瓦茨
- 20: 《理解生产率》学习计划内(四)
- 21: 教务通知(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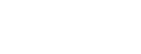
 问答
问答 创业社区
创业社区 创业学堂
创业学堂 讲师团
讲师团 我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