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英特尔(Intel)是较早地体现了在快速发展的行业中,分散式知识如何影响公司战略的实例。《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中,有一篇文章写到英特尔前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AndyGrove)承认:
长期以来,他或英特尔的其他高管都不愿意看到、或者没能看到竞争环境是如何破坏公司作为存储芯片或微处理器主要生产商的战略的。各项目负责人、营销经理,以及工厂监管人员都忙着调整英特尔的战略,把资源从内存转向微处理器。然而,高层管理层者直到两年后才认识到这一事实。格鲁夫承认,管理层可能被“我们的战略说辞所愚弄,但是,那些奋战在一线的人明白,我们必须放弃存储芯片……人们利用他们勤劳的双手来制定战略。我们最重要的战略决策不是为了回应明确的公司愿景而制定的,而是真正了解事情发展进程的一线经理做出的营销和投资决策”。[23]
24、要想利用这种洞察力,组织应当明智地去培养主动性——去培养积极投身于工作的员工。将主动性纳入工作设计(尤其是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就赋予了员工发言权。这种发言权奠定了创新、创造和分担责任或共享所有权的基础。若要发挥这种发言权的优势,领导人则需鼓励协作、分权和担当。广泛培养起员工的主动性,可以使强大的集体智慧服务于整个组织,这种集体智慧远远超越了任何集中管理的系统能够产生的智慧。[24]
25、当然,培养员工主动性的过程中会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不可避免的是沟通困难的问题。也许并不是人人都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如果管理得当,襟怀坦白的讨论甚至争论会得到一些可能你不爱听到的信息,可以改进决策流程。多听听各种声音,你会发现,比起权力、特权或忠诚度来,知识更加重要。使用参与式流程制定的决策,通常都是更好的决策,因为它们基于更多的信息和更少的偏见,并且因为参与性决策的制定过程本身就可以使得决策容易被接受。尽管这样决策会花费时间和资源,但是,员工的参与有助于组织会降低考虑不周的成本,也可以降低员工不接受决策的成本。领导人愿意花时间去明察,了解当代商界的动态,便能发现推行权力下放原则文化的机会和障碍。
26、管理学者多明尼克•玫勒(Domènec Melé)考察了Fremap(一家西班牙非营利性互助保险公司)从过于僵化的官僚主义结构转变为较为灵活结构的过程。在改进了的结构中,工作设计考虑到人的因素(即,使工作更有意义)。玫勒注意到,在改进以前的管理结构中,一份保险文书需要经由八位员工之手,每一位员工只解决索赔工作中的一小部分。在确立了权力下放原则之后,大多数情况下,一位员工就可以处理整个索赔过程。员工变得更有积极性,质量得到改进,客户满意度有所提高,Fremap公司也得到蓬勃发展。[25]
27、显然,这是权力下放原则的一个企业案例。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应用权力下放原则唯一或主要的理由,则低估了该原则的道德重要性。权力下放原则不止是为了经济绩效和组织卓越。在工作场所真正应用权力下放原则要求正确理解人性。26我们认为,要真正运用权力下放原则需要管理者将人视为企业核心的管理信念。为了确立这种信念,领导人需要超越学历和领导力培训的认知,还需要明白权力下放原则的精神和道德根源。(参见第2章)
历史渊源
28、权力下放原则必须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使用,但是如果企业领导人了解一些该原则产生的历史背景,他们会更好地理解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为什么要创造一个人性化的工作环境。权力下放原则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西方政治中在使用。二十世纪,在成立欧盟(1992)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Treaty)中,在联合国人类发展计划的各项报告中,以及在欧盟的基本权利宪章(2000)中,权力下放原则都有迹可循。在现代化的政府结构中权力下放原则也随处可见。比如,根据美国宪法设立的联邦体制就体现了该原则。但是,该原则的源头还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在拉丁语中,单词subsidium最初的含义指备用的某种东西,尤指备用部队:在必要时动用的部队。‘subsidiumferre’表示待在后面,做好准备去帮助那些在前线遇到麻烦的人。” [27]
29、因此,权力下放原则的核心含义是“辅助”,或者“增强”,随时准备着在后面或下面做后援。高一层级的权威机构或社会机构,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协助级别低一层级的(或附属)机构。第一种方式是被动的:在低一层级的机构应该行使自由和发挥主动性的问题上,高一层级的权威机构不要替代前者的主动性。第二种方式是积极主动的:在低一层级的机构无法完成一项重要任务时,高一层级的机构就应该帮助其完成。因此,权力下放原则要求高一层级的机构不是让低一层级产生依赖,而是提供帮助,让低一层级 “通过承担责任来给予自由并积极参与”。[28]
30、20世纪30年代西方极权主义当政时,权力下放原则作为一项正式原则赫然出现在天主教社会教义中。那时,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都在试图同化各国内部的家庭、学校、教会和志愿者团体。由于缺乏充满活力的中间机构,这些政体统治下的社会生活主要以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主导。为了对抗这种势头,教皇庇护十一世(PopePius XI)在1931年颁发了第四十条教皇通谕,其中,他把权力下放原则描述为一种“社会哲学原则”。
31、庇护十一世强调,权力下放原则可以在国家权力过于集中时,保护中间团体(家庭、企业、宗教、教育和志愿者)免于不公平地失去权威和自由。29权力下放原则指导较高层级的社会实体(如国家)支持而不是篡夺基层社会机构和团体应该进行的活动和承担的责任。
32、尽管权力下放原则最初是用于政府中,但实际上它可应用于包括企业在内的任何机构。30在教会的教义中出现权力下放原则的萌芽期,正是产业公司在规模和权力快速增长的时期。当时,管理者大力加强对工人的控制:因为劳动分工而使工人的工作不需要太多的技能,资本所有者不断增加的权力,以及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越来越被动,而集权的公司官僚主义在设计生产体系和工作时,也一味追求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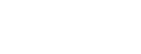
 问答
问答 创业社区
创业社区 创业学堂
创业学堂 讲师团
讲师团 我
我




